开卷有益
悦 读 会 Vol 5
勤于思而敏于行,
读书一直是国富人倡导的学习方式。
读书的态度和类型应当是多元化的,
并不局限于本职工作的领域。
今日点滴的积累,焉知不能在将来聚沙成塔。
“开卷有益”是国富的文化传统,
每一期都会有许多同事通过书评的形式分享好书。
读书使你我辽阔与丰厚,愿读书与我们长久为伴,
让这一天也不断流的潺潺小溪充实思想的河流。
![]()
No.7
June
2020
分享书籍: 《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
[美] 史蒂芬·平克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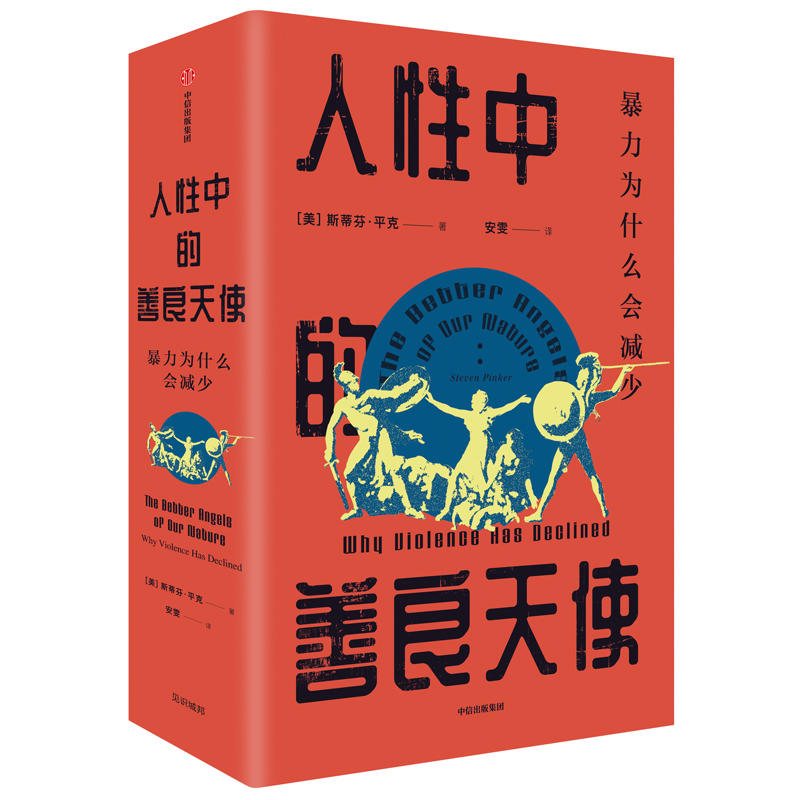
内容简介:今天的人们认为世界到处充满暴力与危险。斯蒂芬·平克在这本令人震撼的著作里告诉我们:暴力其实在减少,我们正生活在历史上特别和平的时代。平克认为,解释暴力减少的关键在于理解将我们推向暴力的“五种心魔”和将我们带离暴力的“四位善良天使”,以及这些内生的心理机制如何影响人的行为。人性并没有改变,但诸多有利的外生力量(如政府组织、识字率、商业和都市的文明进程等)出现,让天使压制了心魔,使我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冲动,对他人怀有同情,宁愿做交易而不是抢劫,揭露那些毒害人心的意识形态,发挥理性的力量,克制暴力的诱惑,导致暴力的减少。
作者简介: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是当今西方世界极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曾入选《时代周刊》“世界有影响力的百人”、《外交政策》杂志的“世界百名思想家”和《前景》杂志“全球思想家”名单。他于1979年取得哈佛大学实验心理学博士学位,后任麻省理工学院心理学教授兼认知科学神经中心主任,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是实验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和科普作家,也是语言学与心智科学研究的领军人物。2016年,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书评作者 | 拾光者
你生活的世界是和平的吗?
面对这个问题,大多数人脑中会飞快地出现这些画面:中东战火纷飞满目疮痍,欧洲难民破坏了社会治安,非洲政权更迭民不聊生,美国枪杀案频频出现,人口失踪频现报端。
想到这里,你不免会失望地摇摇头:自己生活的世界糟糕极了,毫无和平可言。
但让我们回溯一下历史,你可能就会对自己的结论产生怀疑。
亨利·梅因说,战争和人类一样古老,而和平还是当代的新发明。的确,稍微了解一下古代典籍,会发现原来我们的祖先是如此残忍:食人在史前人类中广泛存在;古罗马凯撒大帝的那句:“我来过,我看见,我征服”听起来多么荡气回肠,可无情的铁蹄制造了多少杀戮,涂炭了多少生灵;在《圣经》中,奴隶制还有剜眼睛、分尸、石刑这些酷刑都无可非议,人的生命毫无价值;中世纪基督教王国的文化就是残忍本身,杀婴、屠城、迫害异己比比皆是;观看施暴也是当时的一种大众娱乐方式,人们聚在广场欢呼着观看斩首、腰斩等酷刑的实施。
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对战争的描写也不胜枚举,那句流传千古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吟唱了安史之乱下大唐衰败的悲歌。
走马观花地看完这些让人心惊肉跳的历史,我们是否反而应该庆幸自己生活在这个年代呢?
我们不需要担心被绑架成为奴隶,不需要担心有敌人攻打城池之后进行种族屠杀,不需要担心自己的女儿被劫掠,不用担心因为有不同信仰而被活活烧死、钉在十字架上,也不需要担心因无意冒犯一位男士而必须与他进行生死决斗,更不会有人在广场上热衷于看另一个人被砍头,并发出激动的欢呼声。
不管你承认与否,整个世界的确在向着文明、和平、有序的方向发展。
当今西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认知神经学家斯蒂芬·平克,所著的这本鸿篇巨著《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为我们讲述了人类发展的和平进程,并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平克用详实的数据、严谨的实验结论、旁征博引的社会科学理论,将人类社会历史的画卷缓缓展开。
他告诉我们,人类的确越来越厌恶暴力,当前的社会是有史以来最和平的时期,而且未来会和平。

Photo by Chi Lok TSANG on Unsplash
在大部分生物的世界里,暴力是默认选项,进化中的暴力选择永远是策略性的。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暴力水平的下降,是伴随着社会组织的出现,即中央集权的国家——利维坦。
各种数据均显示,国家形态社会中,战争死亡人数、凶杀率均远小于非国家形态社会中的数字。但世界上第一个利维坦——国家的出现,解决了一个老问题,又制造出了一个新问题,人们远离了凶杀和战争,又被控制在暴戾的君主、神职和贪官污吏手中。我们的和平之路还要走上很远。
漫长黑暗的中世纪结束,欧洲国家的凶杀率下降了90-98%。作者认同《文明的进程》的作者诺伯特·埃利亚斯的观点:这一阶段的暴力下降归因为两个原因:真正的利维坦的出现,经济革命。
欧洲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封建领主和采邑林立的无政府状态后,出现了真正的利维坦,中央集权制国家出现。与此同时,利维坦与商业文明互相关联,合法的选择越具有吸引力,人们也就越不愿意犯罪。
到了启蒙运动时期,我们终于告别了那些骇人听闻的历史。识字的精英阶层的出现,印刷术的发展、书籍报刊的普及,日渐富裕的生活,以及与周边其他社会的出现,使人们意识到了人生命的价值,人道主义革命方兴未艾。
欧洲几个国家在17世纪禁止驱巫,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就不再有宗教杀戮,酷刑的种类大幅减少,死刑数量急剧下降,奴隶制相继被废除,伴随民主的传播、贸易和商业的扩张,以及国际组织的成长,我们迎来了很长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
再来看看大型战争。大国之间的战争破坏力强,影响范围广,是当之无愧的绞肉机。
幸运的是,有记载以来的数据统计显示,大国之间的交战时长、交战数量、每一场战争的死亡人数等等指标均呈现了显著下降。大规模战争的下降,极大地降低了世界的暴力程度。
你可能会有疑问: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难道不是逆了历史规律?
其实仔细研究历史数据,你会发现20世纪绝不是最血腥的历史时期。衡量死伤人数要以当时的人口基数来计算。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人口总量是公元1世纪的15倍之多。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按照调整后的暴行损伤程度进行排名,中国唐朝时期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高居榜首。当时的唐朝损失了2/3的人口,即当时世界1/6的人口。
过去几十年中,世界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地区冲突,小国之间的战争,内战,种族清洗,恐怖主义,大屠杀等等暴力行为。关于这些的新闻似乎每天都会在媒体上滚动播放。
但让人惊讶的是,统计数据显示,这些小范围的冲突也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人类在围剿大范围暴力方面取得了节节胜利,现代社会权利革命也把我们引领向更文明的方向。
私行的数量到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接近于0;被谋杀的人数下降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数量级;人们允许异族通婚;女性地位逐步提高;杀婴、虐童、欺负弱小的数量下降了三个数量级;对待LGBT更加宽容,甚至部分国家宪法承认了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对待动物,我们也更加有爱心。

Photo by Hanna Morris on Unsplash
以上的数据及趋势提示我们,人类的各种暴力行径在显著减少。那么到底是哪些原因使得人类脱下了原始的外衣,变得彬彬有礼,不那么暴虐嗜血呢?
首先,我们要从暴力的产生原因说起。
人一生最暴力的阶段不是成年,也不是青少年,而是两岁。人类内心对暴力行为的信息充满渴望。我们不是长大之后学会了攻击,而是在成长过程中慢慢学会不去施暴的。
这说明,暴力在生物之中是有很强的生理基础的。哺乳动物的大脑里有不同的回路处理各种不同的攻击行为。比如人类,覆盖在眼眶骨架上的“眶额皮层”就与人的情绪相关,若这部分受损,则人会变的非常暴戾。
但暴力的原因绝对不可能是单一的,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杀人狂魔。暴力不仅有生理根源,更有心理学的因素。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高度总结了人类存在暴力的原因:收益——掠夺性攻击,安全——先发制人的攻击,荣誉——报复性攻击。平克引用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的观点,将暴力动机按照心理因素更加细分成了通俗易懂的五类。
第一类是实用性、工具性的暴力,称为“捕食”。
这是人们为了追求某种目标时采用的手段。在这种行为下,施暴者没有仇恨或者愤怒的情绪动机,只不过是为了达到目的选择了一种捷径手段罢了。比如原始部落为了争夺领土兵刃相见;罗马人镇压行省的起义;劫匪为了避免被警察发现伤害甚至杀害了受害者等等。
第二类是追求控制,称为“优势”。
这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暴力形式。人们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或是展现自己的控制欲,而展开的暴行。比如主权国家的侵略战争,美国街头的暴力行为等等。如果统治者具有这种暴力倾向,则后果会非常严重,典型的例子如萨达姆·侯赛因,穆阿迈尔·卡扎菲,希特勒等等。
第三类是“复仇”。
血债血偿几乎是全世界95%的文化都明确赞许的准则,在世界范围内,10-20%凶杀案的动机是复仇,绝大部分校园枪杀案和个人爆炸案的动机也是复仇。对一个集体的不满,如恐怖主义,危害城市等行为,也是复仇的因素造成的。
在“道德标尺的偏差”作用下,复仇者总是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因此复仇并没有像其他种类的暴力行为那样建立了均衡的态势。
第四类是毫无理由地制造痛苦,享受伤害他人的快乐,即“施虐”。
宗教审判中的裁判官、战争中烧杀劫掠强奸妇女的士兵、罗马斗兽场的观众,都是施虐的心理因素在作怪。人们对生命脆弱性的病态好奇,自我的优势感,对恶人受到惩罚的复仇感等等动机,是人们在观看他人受到痛苦得到满足的解释。
第五类也是后果最严重的暴力根源,“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终极目标是理想化的,是要实现更大的善。比如南京大屠杀,纳粹主义,种族清洗。这种暴力通常是通过群体完成的。
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群体能够让思想发生各种病态的变化;人们聚成大众后悔变得更加无知;而且从众心理也使得很多不相信某种信条的人,强行去信奉某些理念。群体因为“意识形态”屠害对方时,展现的残忍更让人心悸。
在面对无辜的生命血流成河惨烈景象时,施暴者同样会用“道德标尺的偏差”来获得心理上的释然。他们会用委婉的辞藻描述伤害;从小步的暴行到逐渐泯灭人性;用“服从命令”这种冰冷的理由来推卸责任;“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但百万人的死亡只是一个统计数字”,施暴者与受害者的疏离使得前者更加冷酷无情;妖魔化被侵害的对象,给自己找到正当的侵略理由。

Photo by Aman Upadhyay on Unsplash
在了解了人类生理、心理上的原罪之后,你可能不免又会感到沮丧:难道自己生来其实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
好在平克又帮我们总结了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这些正面的心里因素制衡着这些心魔,让我们得以控制住自己,不再那么嗜血而骄。
第一个是移情。
移情指的是我们能够置身于其他人、动物或者事物的位置,想象身处其中的感受。移情力强的人,普遍拥有较强的负疚感,同情心。人们在阅读小说、回忆录、文学,观看影视作品的时候,会对其中的人物报以同情,对一个人的同情又可以扩展到这个人所代表的群体。
第二个是自制。
自制作为意志力可以克制大部分放纵行为,大量实验结果也支撑了猜想:自我控制神经机制的软弱很可能导致暴力。
自制力有遗传影响,在生活小节上的自制力培养,可以使自制力成为人的第二本能,并且影响到一个人的风度举止,进而控制着自己的暴力倾向。
说句题外话,除了智商之外,没有其他特质比自制力更能预示一个人的健康和成功了。因此刻意培养自制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是道德和禁忌。
道德是把双刃剑,可以增强人们的意识形态,也可以让人远离毒化的思想。运用得当的情况下,道德的确是推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动力,比如启蒙运动中的人道主义精神,近几十年的权利革命。人口迁徙和社会流动性,以及人们对历史的客观研究,使得道德的标尺远离了社群、权威等带有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趋向于公平、正义、理性。这种道德感增强了同理心,使得人们远离暴力。
第四个是理性。
理性思考与人的认知水平的提高分不开。“弗林效应”告诉我们,人类的智力水平一直在不断提高,人们的认知水平能力越来越强,理性思考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人类的合作能力越来越强,道德关怀的圈子越来越大,对不合理事物的容忍度也越来越低。
例如,人越聪明,越倾向于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在历史上,对经济学的无知结果就是民族暴力和阶级暴力。因为人们认为,穷人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出路,就是干掉剥削者,自己取而代之。当一个社会达到一定文明程度之后,理性是人类得以控制暴力最大的希望。
读到这里,你可能还会问。除了人类智力水平不断提高外,其他心理因素难道是最近几十年才有的吗为什么这些善良天使在几百年前没有遏制住我们祖先的心魔呢?答案是外部社会环境的变迁。
平克认为,这些变化对人类的和平进程产生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利维坦的出现,控制了史前人类的小团伙、部落、酋邦,对劫掠和争斗的压制,使暴力死亡率下降到之前的20%。国家执法力量的统一,使得凶杀率又低至之前的1/30。
文明商贸的发展,消除了发动进攻的动机,相互合作能产生巨大的收益,人们不愿意自己的财产被战争付之一炬。
女性主义的崛起,压制了暴力。男性有更强烈的竞争冲动,为了争夺女性;而女性有更强烈的躲避危险的动机,来保护自己的孩子。因此,直接的政治赋权,男子气概的贬值,女性婚姻自主,女婴生存权,妇女对自己生育权的控制,都使得暴力有显著下降。
圈子的扩大使得人们更多地进行换位思考。识字率、流动性、城市化、大众媒体的发展,都帮助了人们扩大了同情圈。读书的人越来越多,越会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所不齿。实验室研究证明,人们听到或者读到第一人称的故事,可以强化他们对诉说者的同情心。
理性的发展,推动了文明的进程。在充分发展的理性能力以及对合作、民主、古典自由主义和非暴力的接受能力之间,不仅存在相关关系,甚至还存在某种因果关系。
在这些外部因素的作用下,人类真善美的一面被激发出来。
人与人之间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转向了社群,合作,商业互通。
人们对他人的感情更加丰富,暴力行为会受到同样的暴力(法庭、监狱、社会舆论压力)惩罚。
可以说,这样安定的现代社会,是我们祖先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乌托邦

Photo by Jonathan Petersson from Pexels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历史的车辙滚滚向前。岁月抚平了昔日战火纷飞给人类带来的创伤,为后人留下了和平的现在和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现在的和平,可以说是我们的祖先用血肉之躯探索出来的,这也证明了,人类每一份付出都是值得的。
雷马克,肯·福莱特这样的大作家,对近代战争的生动描写的确会让我们对现代社会失望,但古时候绝不是完美的伊甸园,现在也绝不是礼崩乐坏的时代。
相较于过去,对现实存在的少量穷兵黩武,我们无需失望,正如马特·里德利在《理性乐观派》中表达的,不管有什么悲观的论调,经济发展永远是向上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是不断提高的。
同样,在社会秩序上,我们也有理由期待未来是更加民主、开放、和平、政通人和的景象。
···生命有限,让读书使你我辽阔···

版权声明及风险提示
本官网刊载内容仅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和销售要约。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未经版权方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登、发表或引用。